
顏慕庸振興醫院感染科主治醫師
60年代有前輩將感染症知識由美國帶回台灣,以師從劉鈐教授的榮總鄭德齡教授、台大謝維銓教授等人為首,漸漸形成每月一次的病例討論會,到70年代愈發成熟,80年代水到渠成,感染症醫學會成立。
我退伍時剛好中榮建院,擴大招收住院醫師,便加入榮總體系,進入北榮受訓,遇到影響我一生的「人格者」鄭德齡老師。當時鄭老師手下各校學生都有,沒有山頭派系的距離感,在指派我接任高榮急診主任時,老師只交代我八個字:有容乃大、無欲則剛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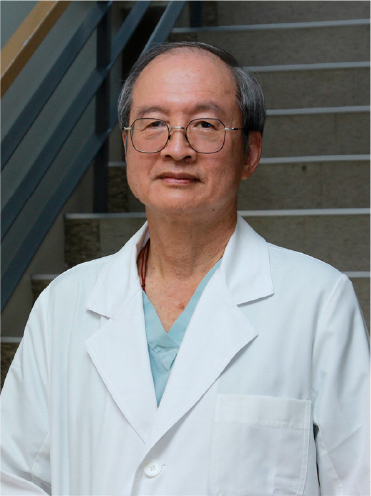
在我眼中,這正是老師身體力行的準則,榮總也才能率先實施抗生素管制政策。當年不分科別,每個醫師都能開抗生素,我在住院醫師時期,抗生素「知識」都來自藥商,可以想像定出管制政策會受到多少利益團體攻擊,能夠成功落實,皆因鄭老師公正無私,所以無畏。
實施抗生素管制後,感染科醫師必然有大量會診,也因此能快速學習,記得我當總醫師時每天查房要看2、30個會診病人,上衣口袋插著屎、尿等各種檢體試管。事實上在專科醫師制度發展後,唯有感染科能看到全人醫療的影子,可惜現在醫師受訓是上網時間愈來愈多、觸摸病人的時間愈來愈少。
我從美國進修回台就去高榮報到,當時高榮剛籌建好,鄭老師擔任院長;同時我也成為感染管制通訊雜誌編輯一員,負責將美國CDC關於醫院感染管制的定義轉譯為台灣醫院感染管制收案定義,開啟台灣制定感染管制指引之大門。
1993年感染管制學會成立,那年我們年輕一輩(張上淳、黃高彬、呂學重等人)很積極,也有前輩不理解,斥責是「不務正業、分門別派、分散感染症醫學會」。其實感染管制和感染症臨床治療完全不同,是另一領域的專業,培訓人員也不只醫師,更重要的還有感染管制護理師,以及醫檢師、藥師⋯等相關人員都可加入。
1995年感染管制列為醫院評鑑獨立項目,是真正落實醫院感控的轉折點。當時我做為代表出席會議,提出感染管制要單獨配分、且是獨立評鑑項目時,現場不少異議,但我提出當時瘧疾院感事件之嚴重性,方才說服眾人:某醫學中心之瘧疾事件肇因於節省成本,電腦斷層檢查時注射顯影劑的導管重複使用,因患者回血污染,致使有病人死亡、有醫師被判刑、自殺的嚴重後果。感染管制之重要性不言可喻。跨入千禧年時,我們提出「零容忍」概念,經過各種外部管理措施(如評鑑)院內感染發生率長期維持固定比率(約3%),這是除錯後得到的品質,也表示沒有達到系統性改善。
而SARS給我們一個面對「零容忍」的機會。
和平封院、全台恐慌,原訂的感管師甄試也因為「太危險」而停辦,但我認為這是我們的戰場。我向醫院請了2周假,由高雄北上,加入抗SARS義勇軍行列。當我進入和平醫院,發現找不到酒精洗手點,得到「穿防護服不需要洗手」的回答!然而早在1980年代,「洗手」就是我們推動院內感染管制中最重要的策略之一,可見觀念與執行間的巨大落差。所以我們從堅持污染分區、醫病分流、酒精洗手點⋯等基礎,到動線管制,迅速控制住醫護人員的傷亡,疫情指揮中心確認此策略有效,於2003年5月23日通令全國推動,2周後,台灣解除了SARS威脅。
感染管制最關鍵的是管理能力,我常講要運用六標準差等管理工具,這也是為什麼很多醫院會由感染科醫師擔任副院長。疫情期間常聽到的「超前部署」,嚴格來說早在1987年感染症醫學會成立時就啟動了,若非這一路打下基礎,無法培育出這一群能隨時上陣的專業人員!
誠然整體防疫表現出色,但不可否認醫界在前線穩定局勢的努力,可我們還是見識到政策修正猶如恐龍轉身的困難,提出專業建議到政策落實平均耗時將近4∼6周(例如由PCR改用快篩)。
在醫界最困難的這三年,就醫人數大減,健保卻並未釋出資源。其實全台感染科醫師、感管師不過上千人,提供穩定的保障,亦是建構醫院、國家不可或缺的戰力。